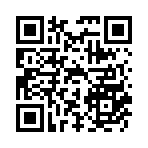強扭的瓜是苦的 家長應讓子女結婚自愿離婚自由
原標題:北京青年報:強扭的瓜是苦的 應結婚自愿離婚自由
我們都知道,婚姻講究的是男女自愿、兩情相悅,而依貌似“般配”的“條件”撮合到一起過日子的兩個人,往往會因為缺少感情而貌合神離,進而衍生成一段孽緣,這樣的婚姻即便是夫妻二人攜手到了白頭,也難有幸福可言,俗語所說的“強扭的瓜不甜”就是這個道理。在當今社會,允許男女自由戀愛,婚姻自主,而當緣分不再時,離婚也不再是困難或難堪的事情。不過,在強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社會里,幸福的婚姻似乎就只能靠運氣,尤其對于并無離婚權的女性來說,忍氣吞聲是基本的生存狀態,最終釀成無可挽回的家庭悲劇。
傳統社會的婚姻,目的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至于說兩個當事人感情如何,是否“琴瑟和鳴”則不在人們考慮的范圍內。所以,大戶人家更在意的是門當戶對,而草民百姓婚姻中的“條件”則更為實際和瑣碎,譬如女方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了,只好將女兒“嫁賣”出去;或者男女雙方家庭處于同樣貧窮的狀態,只好通過“換親”的方式來解決兒女的婚事。由此而結成的婚姻,自然不能奢望其有較高的幸福指數。在這些因各種原因而成就的婚姻里,女性則更有可能成為悲劇的主角,女方的“父母之命”可以說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而受“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觀念的影響,婚后即便是父母知道女兒在婆家受苦,也并不能救其于水火,似乎只有認命這一條路可走。
最近讀了臺灣歷史學者劉錚云教授的《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一書,其中的一篇《也是歷史——清雍乾年間四個女人的故事》,講述的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四個女人的不幸遭遇,一個是為了生活被丈夫讓售他人;第二個是迫于生計被丈夫默許賣奸;第三個是因為堅拒丈夫白日求歡而送了命;最后一個則是自覺與丈夫和好無望,憤而將其殺死。其實這些并非“故事”,因為作者寫作此文時,均取材于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內閣大庫檔案中的刑案數據。
在中國的歷史典籍里,通常記載的是帝王將相的事跡功勛,至于像這四個女人一樣的平民百姓,都屬于“上不了歷史舞臺的小人物,要不是偶然犯下或牽涉重大刑案,他們的一生就像過眼煙云,隨風而逝,不會留下任何記錄”。而通過這些刑事檔案中作者“未做任何剪裁或修飾”的當事人的口供,讓人讀出故事主人翁人生的大不幸。
傳統社會中女人的世界其實很小,她們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幾乎都在家庭這個舞臺上展開,然而,即便在家庭這個小小的世界里,她們也完全不能自主。她們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只是在傳統的碾壓下,不僅不復有實現的機會,有時還會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讓人痛惜。
在《也是歷史》篇里所講的第四個故事中,說的是乾隆年間發生在河南歸德府的一件案子。燕秀的女兒燕氏自幼與楊二小結親,不過從成親之日起,兩人的生活就過得不甚和睦,經常吵嘴打架。由于楊家窮苦,燕氏將女婿“請到”家里一起生活,實際上即是楊二小入贅燕家。后因家庭瑣事,楊二小覺得傷了自尊,遂搬回自己家中居住,而燕氏則長期住在娘家。作為家長,燕秀為了顧及面子,于是將女兒送回夫家,燕氏則因不堪忍受楊二小的打罵又逃回娘家。在“送回”又“逃回”的幾個回合之后,燕氏就做出了謀殺親夫之事。從燕氏的供述中,透露出的是一種對未來生活的絕望:娘家是不能常回去了,和楊二小的日子又沒法安生地過下去,既然如此,倒不如以死亡的方式來斷絕二人夫妻關系。
“故事”的結局是燕氏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燕氏最后依謀殺夫已殺者凌遲處死律,被凌遲處死”。我們學法制史的時候,講到凌遲刑的適用,想象中一般是施用于犯謀反、謀叛、謀大逆的政治犯,或者是殺人越貨的“響馬”“江洋大盜”,而當這樣的極刑被施及一個正當年的花季女子時,那種心驚肉跳的感覺所產生的不適,實在久久難以平復。
這樣的事如果在今天,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男女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伴侶,而“離婚自由”的原則,又使那些“所托非人”之人提供了擺脫婚姻枷鎖并重新出發的機會。只可惜在當時的情境下,似乎所有的人都走入了一條死胡同,正像作者所言,故事中的四個女人雖然遭遇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點:“她們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用現代的術語說,她們沒有‘人身支配權’。在社會上,‘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的觀念將她們完全束縛住;在法律上,她們受到差等待遇。簡而言之,她們是在父親、丈夫的意志支配下生活。”人們雖然都知道“強扭的瓜不甜”的道理,可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人們卻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觀念影響下,一代一代樂此不疲地“強扭著”瓜們,曾經的受害者又不可避免地成為施害者,使得類似燕氏們的悲劇不斷地上演。好在如今社會已進步到了“結婚自愿,離婚自由”的時代,也祈愿燕氏們的“故事”能真正走進歷史。
[來源:北京青年報 編輯:格若]大家愛看